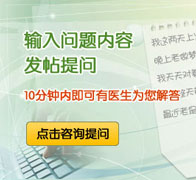王海燕:医者菩提心
人物简介
王海燕,生于1937年,1959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(现北京大学医学部)医疗系。现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北京大学肾脏病研究所所长。历任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会、内科学会主任委员,中华医学会副会长、国际肾脏病学会常务理事,《中华内科杂志》主编及6个国际专业杂志编委。发表学术论文380余篇,出版专著7部。先后获得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成果奖项22项。2006年4月获美国肾脏病基金会卓越成就贡献奖章,2013年6月获得国际肾脏病学会Roscoe R.Robinson奖和首届国际肾脏病学会先驱者奖。
与长者对坐,言语间有真性情,闲话中见大胸襟。
她评论科研工作:“做科研你求什么?写篇文章,单位给点钱,评个什么奖,获得个什么头衔,so what(又怎么样呢)?你的研究能够成为全世界的临床治疗指南,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”
她评论各种肾脏病发病机制研究:“搞清楚这些问题太重要了。如果中国的肾脏病学家能在若干个关键问题上起着系统性引领作用,可就实现了我的‘中国梦’了。”
她评论手头的大项目:“外国的专家就说我:你可胆子够大的啊,钱没到位就敢启动。我回答:一边做一边筹钱吧,哈哈。”
她评论自己的学历:“快要答辩的时候就文化大革命了,我论文印好了都没来得及答辩。现在人家给我填表,都填MD(医学博士),我说我根本没拿过D。”
她指着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三个小猴子挂件,“一个捂住眼睛、一个捂住耳朵、一个捂住嘴巴,意思是不看、不听、不说。我儿子送我的,说我老爱管闲事。”
她展示学生送给她的一张照片,“美国犹他州峡谷里的两块石头,天然的,名字叫balance(平衡)。一个大石头能在小石头上保持平衡,风吹雨打都站得住,这场面见哲理。”
她回忆去尼泊尔时俯瞰喜马拉雅的感触:“天地悠悠,人太渺小。所以不必斤斤计较。”
“中国肾脏病学之母”王海燕教授,刚刚获得国际肾脏病学会(ISN)“R·Robinson奖”和“国际肾脏病先驱者奖”的第一位中国人。对于中国肾病学界甚至医学界而言,这是新闻沸点,也是历史时刻。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奖项,不过当事人却一句都没提起。
“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的东西,不只是专业”
1954年,17岁的王海燕成为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的一名新生。由于个人成长始终和密集的政治运动相伴随,大学并没有将她的职业理想清晰化。“我是1959年毕业分到北大医院内科的,老师是中国肾脏病学的创始人王叔咸教授。那时,全世界的肾脏病学研究都刚刚开始。
1962年,“七千人大会”的召开,学术与科研开始在政治运动的缝隙中泛出绿意。王海燕在这一年考上了王叔咸教授的研究生。
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导师教给她的第一课。
一个例子是读书。“他自己很刻苦,每个星期天上午都要去图书馆看书。他到图书馆去看书,我们学生也得跟着去。还得向他汇报,这个礼拜我看了什么书,读了什么文章,有什么收获、有什么未解决的问题和挑战。要不去星期一来了他就会问:‘这个星期天,你怎么没去图书馆啊?’”
另一个例子是讲课。“当时我们毕业才三年,就开始给大学生讲课。那时候也没有幻灯,怎么写板书,什么内容写上、哪些擦掉,到下课的时候要如何把要点都留在黑板上,他都要一一传授。”
王海燕的第一堂课是给学生讲肺炎。尽管在老师指导下已经多次彩排,但正式上台、面对百余名学生时仍不免紧张,恩师在最后一排指指自己耳朵提醒她提高音量的画面,她终身难忘。
“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东西,不只是专业。他的治学严谨、他的低调谦虚、他对学生既严格又爱护的态度——总之是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。”
她坚决否认“中国肾脏病之母”的称谓。她将导师那一代人称为中国肾内科的第一梯队,将自己这一代人称为第二梯队,将今天自己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称为第三、第四梯队。王叔咸教授身上的优秀品格,经由她的传承和光大,已经成为了这个团队的基本精神和集体操守。
会议室里,摆着王叔咸教授的铜像。后继者的所有探讨、交流、会议和科研,都像在他的目光下进行。立铜像的人,当年那个懵懂中来到北医的小姑娘,现在已经在北医系统里工作了半个多世纪,为肾脏病学奉献了五十多年,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泰斗。
“今天你去医院看病,不应再有任何医生笼统地诊断你是‘肾炎’或‘尿毒症’”
1979年,王海燕已近不惑。和许多从运动时代走过来的同龄人一样,她恐怕从未曾想过自己会走出国门。
“事情很突然。当时我还在莫干山参加内科学编写工作。一天黄昏,接到单位一个电话,让我赶紧回北京参加考试——教育部选拔第一批出国学习的人员。”
回京的火车买不到坐票,王海燕站了一晚上,借着昏黄的灯光读她临时买的《广播英语》。作为一个受俄语教育的“文革”前大学生,英文考试将是最难的一关。
离考试还有一周。她找来外交学院的朋友,找资料、讲语法、练口语。为了集中精力,特意从家里搬到集体宿舍,睡觉时枕头边也要开着那个砖头大的录音机。“就这么突击了一个礼拜,就去考试了。”
并不顺利,但涉险过关。三十多年后,老太太用纯正的美国腔评价当年,“考英文就是考你的feeling(语感)。但英文基础太差的时候,你总在那想,书上是怎么讲的啊,填卷子就非常慢了。成绩挺差的,但总算是达到那个分数线了。”
她选择去洛杉矶的UCLA-Harbor医疗中心深造,导师蜚声业界,有MR Glomerulus(肾小球先生)的雅号。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访问学者,她是当地罕见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。
“我一去,好多美国人、美籍华人都来看我。我的导师见人就介绍我,哎,她是从the People’s Republic of China(中华人民共和国)来的。我给家里写信,说我现在就像大熊猫一样,哈哈。”
从另一个角度讲,这也意味着,她注定要扮演一个拓荒者的角色。“当时咱们的肾脏病学专业,和国际上差得太远了。那时咱们就认识两个病,一个肾炎,一个尿毒症,再细化就说不清楚了。”
当时,国际上推动肾脏病研究发展的路径有两条,一条是生理学,一条是病理学,王海燕选择了后者。刚刚迈出国门的中国医务工作者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“如何治病”,病理学可以很直接地关系到对病人的诊断,并通过基础医学来推动临床科学发展。
她将很多概念带回了中国。首先,她率先在中国建立了各种肾病的动物模型。作为一个中国的临床医学家,她在引入和普及国际经验的同时,也在革新和丰富这种方法。
(责任编辑:好医师网)- :上一篇:大连沙河口区的皮肤科医院在哪里
- :下一篇:【走近大家】王海燕:医者菩提心(1)